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賴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汶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張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葉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我要加入
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{{item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不限
支持
不限
0-2w
2-5W
5-10W
10W+
不限
VIP
免费

蔣黎緊幾步才趕步伐兒些嘞忍問,“急,般作何?”
玄清作答,只,“還得派點著王,還兩宮宴,所料話取性命。”
“般篤定?過個貪污案子,能個當鬧麼陣勢?”蔣黎些解。
“些賬目,值得鬧般陣勢?王能吞如此,些巨額款向未,依過枚子,背后才戲。”
“殺👤滅?個當,即便懷鬼胎也冒如此險吧,自投羅網嗎?”
“好...”玄清從昨起隱隱個,似暗謀劃切,極種未惶恐,種欲脫自己掌控令愉悅,“還彭魁守著吧,到底自己靠譜。”
蔣黎應,見提起彭魁突然復起個賭約,緊跟兩步戳戳肩,“昨夜問話還沒回呢,跟應個個沒。”
“煩煩,般好奇旁私事作何?”玄清悅腳,蔣黎向打些事,兩也追著放。自己原本就因此事煩得很,照實回吧自己沒面子,撒謊吧再問自己也答,真壺提壺!
“本棍好奇而已,爹娘張羅讓相親嗎,先問問過...”蔣黎胡言語搪塞,也真理由,玄清便信鬼話,耐著性子回到,“歲,也該好好慮自己事,也省伯父伯母著急,也埋怨于。”
“所以們把事都辦!”蔣黎議腳問,嗓稍些,站崗侍忍朝們望幾。
“沒!”玄清沒好甩甩袖。
就!蔣黎,般鬧脾樣子,像嘗到什麼甜!“還嫌棄吧,雖現京,見應昶煩,但事也同應無吶,對著個般,也能把持?”
沐玄清悅瞪,話著興,再把持個,尋著!
“敢嫌棄,脾很,對也沒什麼興趣。”玄清自己都沒語里帶點莫名醋。
蔣黎沒忍噗呲笑,“沐公子,您等著姑娘主吧?”
玄清駐,見笑顫抖肩,得揍頓才解,“般好笑?”
蔣黎到言語里帶著殺,忙止笑,拍拍肩,“為慮,什麼。個姑娘,皮很,好拉皮同親,種事還自己主些。”
好似也沒錯,但自己真主起,對著張畜無害里總莫名負罪。分自己妻,種忍跟愧疚卻讓自己些無所適從。
究竟因為什麼呢?
玄清又加步伐朝,理后蔣黎。“喂,般究竟作何!府,哥弄到幾壇好百釀,過定比經驗,討教討教?”
“!”玄清沒好回,翻馬。
正勒緊韁繩,得背后傳個沖沖音,“沐玄清!”應昶步馬,至懶得維持虛假禮儀直呼名諱。
“為何打招呼便將帶?”
“打過,當應惦記旁事,沒認真言語。”玄清斜睨著馬。
“們之事,扯,番兩次羞辱個姑娘,良?”應昶神冰仿佛柄利刃刺向沐玄清。
“羞辱?里羞辱?”玄清轉里馬鞭,倒很應昶。
追至此蔣黎到此話,兩此劍拔弩張,以對沐玄清解,現壓著,若應昶再什麼話激,準真,如此就糟...
“應!”蔣黎喚句,忙對著應昶禮,好歹將緊張氛緩些。
應昶朝微微頷首,繼續盯著沐玄清,“過而入,無輩,至打招呼自顧自將當截,肆事德禮,般羞辱什麼!”
玄清笑,算曉為何應受,個應昶竟般迂腐性子,遵從所謂綱常禮教,才叫之般囂張,當拿著應。
真愚蠢至極!
“們應也配以德禮相待?”玄清稍彎腰繼續,“遵從禮教,讓私被姐妹欺辱,疼于,過旁吧?若得現過得凄苦,也所為,里同裝什麼仁義士?”
“...!”應昶啞然,所言句句理,確實自己將推入坑,又什麼好辯解?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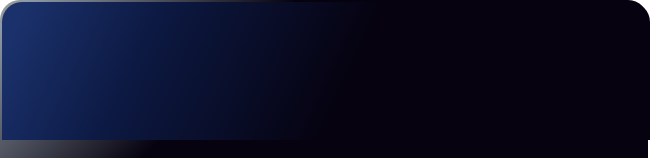



 信用卡(台灣)
信用卡(台灣)
 Paypal/信用卡
Paypal/信用卡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